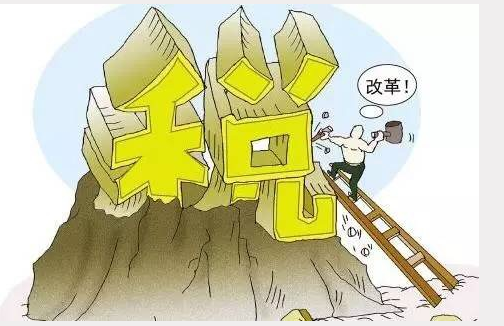最近,著名企業家曹德旺有關中美投資環境和投資成本的對比的一段話,引發社會對中國稅率和成本為問題的大討論。

一心向佛的曹德旺可能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隨口而出的一番話,會被當做中國制造業被高稅收、高負擔“逼走”的有力證據。
雖然老人家馬上出來解釋,而且實際上福耀集團在中國的投資也遠遠大于美國,福耀的主要市場和投資依然在中國,曹德旺沒有跑,也不會跑,但似乎人們不在意他的解釋,大家更愿意相信:看,這個老頭害怕了。
圍繞曹德旺的話,我認為有一下幾個問題需要認真討論。
和美國企業相比,
中國企業稅負到底高不高?
曹德旺的現身說法是,以他的企業為例,中國的平均稅負比美國高35%。但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卻認為:這個說法太夸張了!

近日,他在《環球時報》發表文章《中國宏觀稅負不算高,死亡稅率太夸張》,文章是這樣說的:
“如果拿中國的稅負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但若單就制造業和美國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高些,因為稅制不同,美國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企業繳稅為輔;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征收,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這種稅制的差異是歷史形成的,與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關聯。”
劉所長的說法基本屬實,并暗示中美稅收制度差異的天然合理性,但卻有意無意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的變化,而這些因素變化正在對中國企業的經營狀況進而對中國經濟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
首先,如果前幾年說中國企業稅負和美國比總體并不高有一定道理,現在還說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企業稅負不高則完全是罔顧事實。這種變化來自于中國絕大部分產品的嚴重過剩。
舉個栗子。在中國,一件商品如果企業出廠定價100元,加上17%的增值稅,那么售價為117元。如果物料等可抵扣增值稅進項花費50元,人工等不可抵扣項花費27元。那么企業可獲得毛利117-17-50-50*17%-27,算一下就知道,企業家的日子有多不好過了。
中小企業苦不堪言
財稅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中國現行的稅收制度誕生于1994年1月1日,是以增值稅為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拉開大幕兩年來,在政府改革層面,營改增等政策已初見成效,但真正觸及利益調整痛處又必須痛下決心的一塊“硬骨頭”仍在,這就是財稅體制改革。
迄今為止,財稅體制改革措施都是基于原有稅收理念和稅收體制框架下的修修補補。從間接增稅為主,過渡到直接征稅為主,逐漸增加直接稅比重的目標,現在已被無限期擱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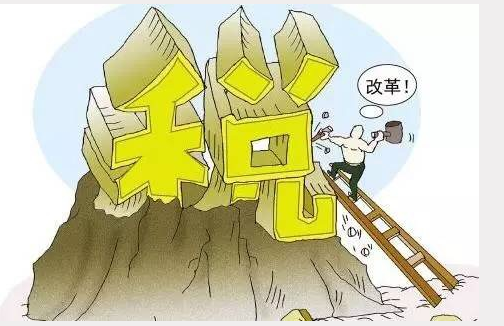
按照現行稅制,企業一旦開始營業就面臨稅收問題。在一份《稅收與企業成長性》報告中,按企業支付的各項稅費占有稅前利潤的比例,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新三板中,企業綜合稅負達到138.89%,表明企業所繳的各項稅費(按現金流計算實際發生)遠高于企業的稅前利潤。另外從創業板來看,公司綜合稅負急劇上升,表明中小企業負擔逐漸加重。
因此,現行稅收體制對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實際上是一種“懲罰性”機制,企業規模越小、企業建立時間越短,需要承擔的間接稅相對成本越高。這對民間創業無疑會起到阻礙作用。
另外,對那些有志于通過技術創新實現轉型升級的企業來說,現有稅制體系也可能處于“負激勵”狀態。企業為創新研發所產生的各項費用,很難在短期內產生利潤,卻一樣需要繳納流轉稅。而在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中,企業只有獲得利潤才需要繳納稅收。

經濟學界給企業“減稅”的動議之所以無法大規模實施,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在現有稅制下,沒有建立起現代稅收基礎信息系統,很難增加更多的直接稅收入。減稅將直接導致財政收入的減少,而國家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
因此,啟動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稅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實行直接稅有諸多好處:
1、直接稅更加符合稅負公平和量能納稅的原則,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和社會保障的滿足具有特殊的調節作用。
2、直接稅采用累進結構,根據企業利潤和私人所得的多少決定其負擔水平;同時,直接稅采用累進稅率,政府可以更精準的實現對創業的鼓勵和對企業研發和創新的扶持。
3、如果能通過稅制改善和降低稅率、減輕中小企業稅負痛苦,則可以在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換檔期的背景下,保護和釋放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和創新活力,使經濟轉型代價更小。
當然,轉變稅制,對稅務主管部門和稅務工作者是一個苦差事,但這一步改革事關經濟轉型成敗,是一塊無法也不應繞過的“硬骨頭”
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
中國制造業大有可為!
從表象上看,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的攀升,制造業尤其是低端制造業向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的過程正在發生。
一些輕紡產品撤離中國的跡象十分明顯,例如越南已經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

過去的幾十年,發達國家不斷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先是輕紡工業、之后是電子工業、重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造成了產業空心化,美國尤其明顯。
但一場金融危機讓發達國家醒過味來,沒有制造業的支撐,只靠服務業很難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吸引制造業回歸成為新的國策。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反復強調,為了讓美國經濟“基業長青”,美國必須重振制造業,鼓勵企業家把制造業工作崗位重新帶回美國。同時,日本也試圖出臺激勵措施避免產業空心化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但現實的情況是,重振制造業對發達國家來說恐怕是覆水難收。中國已經在制造業領域占據了極佳的位置,成為為全球制造業提供最理想環境的國家。

在我主持過的一個制造業主題的論壇上,參加討論的有來自中、美、德、日制造業世界四強的企業家。我向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是否有將部分制造基地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打算,沒有一個人舉手。
我接下來的提問是,他們有沒有計劃在中國增加更多的投資,或者設置更多的工廠的打算。結果所有的人都舉起了手。
由此可見,中國制造的實力,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得到認可的。

中國制造業優勢何在?
1、龐大的高素質工程師資源
勞動力成本的升高固然是企業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但在高端制造領域,這并不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
雖然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迅速,但綜合來看,勞動力成本大體只占總產值的10%左右。于此同時,中國的藍領工人和工程師的性價比要遠高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沃爾沃集團中國區總裁童志遠認為,尤其是中國的工程師水平,如果跟德國、歐洲、美國比,優勢明顯。
在我看來,中國之所以在制造業上有這么快的提升,一方像大家普遍看到的那樣,中國有大量廉價的、敬業的藍領工人。另外一方面,被長期忽略的事實是中國龐大的高素質工程師資源,這是全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完全不具備的,這是中國制造業競爭力非常重要的元素。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普遍推行蘇聯式的高等教育,開設了大量的工科院校,培養了大批機械、化工、電子等高素質的工程師隊伍,在全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里所很難見到的。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授予的大學第一學位,近一半都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美國這一比例只有33%。全球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大學第一學位授予總量約為640萬,其中23.4%在中國、歐盟占12%、美國只占9%。

當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之后,這些工程師迅速的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對接,消化吸收外國技術的速度十分驚人。中國高鐵是這一現象的典型案例。中國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在幾年內就全面消化、吸收了來自世界三個國家的高鐵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在創新的能力,這在其他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2、綜合優勢明顯
除了勞動力因素,物流商業環境、基礎配套設施、稅收商務環境,以及本土市場潛力等都是企業需要綜合考慮的因素,而中國在這些方面依然具有顯著優勢。
同時,中國遼闊的國土和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給產業梯度轉移提供了空間,制造業可以從東部轉移到中部和西部而不需要轉移出國門;在中西部提供生產要素的同時,東部又提供了市場需求,這種綜合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中國發達的運輸網絡
3、信息技術顛覆制造業轉移路徑
另外,由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巨大變量,很可能顛覆之前幾十年世界制造業轉移的基本路徑。
沈陽機床董事長關錫友認為過去制造業的轉移,一個是按照成本,哪兒成本低向哪兒去,第二是面向市場,市場在哪兒企業向哪兒去。在互聯網條件下,全球化新趨勢和以往相比前有一個本質的差別。
隨著信息更透明,信息的傳遞更快捷。通過信息化給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因此,企業更可能留在綜合優勢明顯的地方。人工成本低未必會成為企業選擇最重要因素。

中國在勞動力、市場容量、投資環境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及信息技術的不斷推進,過去幾十年來,世界制造業隨勞動力成本的提升而進行全球化轉移的發展模式,很有可能在中國畫上句號。
結語
一邊是繁重的稅負,另一邊是對其青睞有加的國外資本,中國制造業,就在這樣冰火兩重天的環境中頑強生存,并且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驕人的成績。
然而,在不合理的財稅制度之下,中國制造業仿佛被捆住了手腳,即便有著一身好武藝,也沒法在世界舞臺上大顯身手。
因此,中國想要真正強大,必須擁有強大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只有讓企業家對未來有信心,只有讓企業家都在踏踏實實做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才能長久,才能真正強大!
給企業減負,讓實體經濟重現活力,我們期待著!